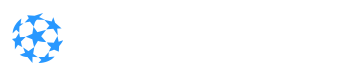校堂歌丨“用一颗初心,走最远的路”强军报国
作者:365bet亚洲体育 发布时间:2025-10-21 10:32
 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成立,简称“哈军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全国之力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军事工程技术学院,也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军事工程学院。从1953年建校,到1966年更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1970年主体南迁并增设其他学校,学校强军报国的信念始终传承下去。 2013年,哈尔滨工程大学在哈尔滨军工原址上修建了哈尔滨军工纪念馆。它包含数千件物品,体现了一代代师生扎根黑土地、报国强军的忠诚和责任。点击视频eo ↓ 现在,步行穿过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军工纪念馆。哈尔滨工程大学教学楼绿檐青瓦,雄伟、庄严。自1953年竣工以来,嘹亮的军鸣声一直是学校的钟声,已经70多年了。哈尔滨工程大学退休教师、学校终身名誉教授李继德:军号的声音,就像命令,是一种号角。哈尔滨工程大学学生白新宇:铃声就是我们上课和下课的号角。有时候,我坐在教学楼里,我想,那些前辈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这里读书呢?也许我没有比他们更努力。这时我想,我越努力,就越能离他们更近。号角一响,使命召唤。在哈萨克斯坦军工纪念馆里,“第一阶段中美武器装备对比表”抗美援朝战争”让世界惊叹。中国空军0架、海军0架、坦克0架、战机0架、舰艇0架……在多种装备下,中国志愿军浴血奋战,惨败强敌。这所诞生于炮火中的抗美援朝学校,敢为人先,极限困难,创造了“从0到”的奇迹。 1》一一:全国第一个风洞群、第一艘水翼快艇、第一艘两栖坦克、第一台舰载电子计算机……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工程学院水声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华正宇:当时那些学生再苦再累,也要啃最前沿的技术。“想着党,报效国家, 强军”是哈萨克斯坦军人刻在骨子里的信念儿子。哈尔滨军工第一批毕业生毕业设计。虽然纸张已经泛黄,但字里行间依然充满了青春的激情:如何增加火炮的射程,如何提高装甲车摧毁障碍的能力……他们的项目直接面向国家对军队的战略和作战需求。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博士生 赵望源:哈尔滨的军工一旦建立起来,我们就不会亚洲人手、设备、财力都稀缺。但在这样的国家需求背景下,我们哈萨克斯坦军队第一批工业学生结束的项目开始解决军队的各种需求。他们的设计、防御和终极技能都与我们国家的战略需求密切相关。哈萨克斯坦军工工业筹建初期中央政府搬了整个国家,但师资不够,所以从大学、科研机构和军队中选拔教师和助教。教材难找,出国进修的老师们回国后都会手抄外文资料,翻译成书。他们不畏艰辛,锐意进取,哈尔滨军工有限责任公司的蓝色道路上钻满了钢铁。哈军工纪念馆馆长李红:这是杨士颉院士用四种文字写的科研手稿。 1956年,杨士颉院士赴苏联留学。他抄写了列宁图书馆的技术资料。我们还问院士为什么要把这样的技术资料抄成四种语言?他表示,只有掌握了语言,才能准确理解最前沿的技术l 信息。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 1952年,杨士颉调往哈萨克斯坦军工,后又被派往苏联研究国家急需的水声学。他将穆拉转向天文学和物理学,加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回国后,他主导创建了首个理工结合、服务国家战略的综合性水声工程专业,填补了国内空白。他的研究成果也为可提交的“蛟龙”定位系统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工程学院副教授 曹忠义:杨士颉院士常说,天塌下来,高者还得拼!如果你不承担责任,谁来承担?杨时锷院士已九十高龄,仍站在讲台上为学生授课。他被礼貌地称为学生们口中的“坚持到底的学术”。他的一言一行,闪耀着跨越时空的哈萨克斯坦军工精神。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教授 李帅:杨士颉院士常说,基本的技术装备是买不到的,我们只能靠自己实现从0到1的成功。我国只有掌握了这样的技术,我们的国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从哈尔滨军工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再到哈尔滨工程大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一”始终指引着学校的发展。进入新时代,从研制可提交的“悟空”无缆深海到打破万米深海潜水纪录,再到自主规模化关键技术助力我国大保有量邮轮“阿达·魔都”号成功研制,在研制中成为我国第一拥有量的邮轮。哈萨克斯坦有着良好的学习传统和军工传统,体现了国家和军事的强盛。在杨时燮院士苦苦挣扎的水生楼医生办公室一角,记者看到了学生们写下的一句话“用初心,走最远的路”。它是哈萨克斯坦军工精神的基石,也是跨越时空的遗产。哈尔滨工程大学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杜雪:今天的幸福生活不是空中楼阁。许多人匍匐前进,从后面支持我们。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接力棒。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也是我们下一代向前迈出的一步。有一句话我很喜欢,那就是“成功不一定是我的,成功一定是我的”。我们的国家一步步不断前进,必须有一代又一代的接力。(央视记者潘红旭 马里黑龙江)
编辑:郑建龙
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成立,简称“哈军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全国之力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军事工程技术学院,也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军事工程学院。从1953年建校,到1966年更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1970年主体南迁并增设其他学校,学校强军报国的信念始终传承下去。 2013年,哈尔滨工程大学在哈尔滨军工原址上修建了哈尔滨军工纪念馆。它包含数千件物品,体现了一代代师生扎根黑土地、报国强军的忠诚和责任。点击视频eo ↓ 现在,步行穿过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军工纪念馆。哈尔滨工程大学教学楼绿檐青瓦,雄伟、庄严。自1953年竣工以来,嘹亮的军鸣声一直是学校的钟声,已经70多年了。哈尔滨工程大学退休教师、学校终身名誉教授李继德:军号的声音,就像命令,是一种号角。哈尔滨工程大学学生白新宇:铃声就是我们上课和下课的号角。有时候,我坐在教学楼里,我想,那些前辈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这里读书呢?也许我没有比他们更努力。这时我想,我越努力,就越能离他们更近。号角一响,使命召唤。在哈萨克斯坦军工纪念馆里,“第一阶段中美武器装备对比表”抗美援朝战争”让世界惊叹。中国空军0架、海军0架、坦克0架、战机0架、舰艇0架……在多种装备下,中国志愿军浴血奋战,惨败强敌。这所诞生于炮火中的抗美援朝学校,敢为人先,极限困难,创造了“从0到”的奇迹。 1》一一:全国第一个风洞群、第一艘水翼快艇、第一艘两栖坦克、第一台舰载电子计算机……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工程学院水声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华正宇:当时那些学生再苦再累,也要啃最前沿的技术。“想着党,报效国家, 强军”是哈萨克斯坦军人刻在骨子里的信念儿子。哈尔滨军工第一批毕业生毕业设计。虽然纸张已经泛黄,但字里行间依然充满了青春的激情:如何增加火炮的射程,如何提高装甲车摧毁障碍的能力……他们的项目直接面向国家对军队的战略和作战需求。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博士生 赵望源:哈尔滨的军工一旦建立起来,我们就不会亚洲人手、设备、财力都稀缺。但在这样的国家需求背景下,我们哈萨克斯坦军队第一批工业学生结束的项目开始解决军队的各种需求。他们的设计、防御和终极技能都与我们国家的战略需求密切相关。哈萨克斯坦军工工业筹建初期中央政府搬了整个国家,但师资不够,所以从大学、科研机构和军队中选拔教师和助教。教材难找,出国进修的老师们回国后都会手抄外文资料,翻译成书。他们不畏艰辛,锐意进取,哈尔滨军工有限责任公司的蓝色道路上钻满了钢铁。哈军工纪念馆馆长李红:这是杨士颉院士用四种文字写的科研手稿。 1956年,杨士颉院士赴苏联留学。他抄写了列宁图书馆的技术资料。我们还问院士为什么要把这样的技术资料抄成四种语言?他表示,只有掌握了语言,才能准确理解最前沿的技术l 信息。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 1952年,杨士颉调往哈萨克斯坦军工,后又被派往苏联研究国家急需的水声学。他将穆拉转向天文学和物理学,加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回国后,他主导创建了首个理工结合、服务国家战略的综合性水声工程专业,填补了国内空白。他的研究成果也为可提交的“蛟龙”定位系统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工程学院副教授 曹忠义:杨士颉院士常说,天塌下来,高者还得拼!如果你不承担责任,谁来承担?杨时锷院士已九十高龄,仍站在讲台上为学生授课。他被礼貌地称为学生们口中的“坚持到底的学术”。他的一言一行,闪耀着跨越时空的哈萨克斯坦军工精神。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教授 李帅:杨士颉院士常说,基本的技术装备是买不到的,我们只能靠自己实现从0到1的成功。我国只有掌握了这样的技术,我们的国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从哈尔滨军工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再到哈尔滨工程大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一”始终指引着学校的发展。进入新时代,从研制可提交的“悟空”无缆深海到打破万米深海潜水纪录,再到自主规模化关键技术助力我国大保有量邮轮“阿达·魔都”号成功研制,在研制中成为我国第一拥有量的邮轮。哈萨克斯坦有着良好的学习传统和军工传统,体现了国家和军事的强盛。在杨时燮院士苦苦挣扎的水生楼医生办公室一角,记者看到了学生们写下的一句话“用初心,走最远的路”。它是哈萨克斯坦军工精神的基石,也是跨越时空的遗产。哈尔滨工程大学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杜雪:今天的幸福生活不是空中楼阁。许多人匍匐前进,从后面支持我们。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接力棒。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也是我们下一代向前迈出的一步。有一句话我很喜欢,那就是“成功不一定是我的,成功一定是我的”。我们的国家一步步不断前进,必须有一代又一代的接力。(央视记者潘红旭 马里黑龙江)
编辑:郑建龙 下一篇:没有了